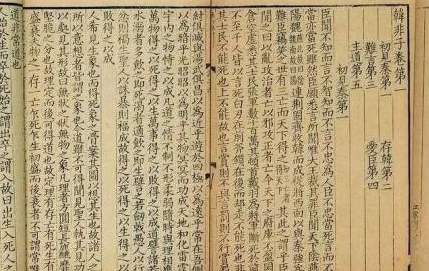
所以韩非很难说是一个达观的前史进化论者,他乃至不是一个逾越主义者(像他所推重的老子那样站到道的高度对实际的漠然置之和疏离),他更像一个冷峻而抽离的有用主义者,对社会前史的开展既不做达观的等待,也没有失望的失望,而是对其不断改变、紊乱纷争的实际进行客观、镇定的描绘。
所以民智进化也好、退化也好,前史前进也好、让步也好,实则不是韩非重视的要点,而他真实重视的其实仅仅他的政治建议得到辩解:一是变法,二是法治。
他关于前史开展的知道与其说是进化,毋宁说是变易,与儒道无限留恋的复古情结不同,韩非对古代社会的前史回忆更是一种对当下紊乱实际的照顾,对他政治理论的回应:由于古今异俗、世情时变,故应变法以应变;由于民智未萌的年代一去不返,调和温情的德治也不行复现,所以当下大争之世,只能以惩罚齐民之轨。

